
作者简介
陈守湖
陈守湖,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师从冯黎明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新闻传播研究。
内容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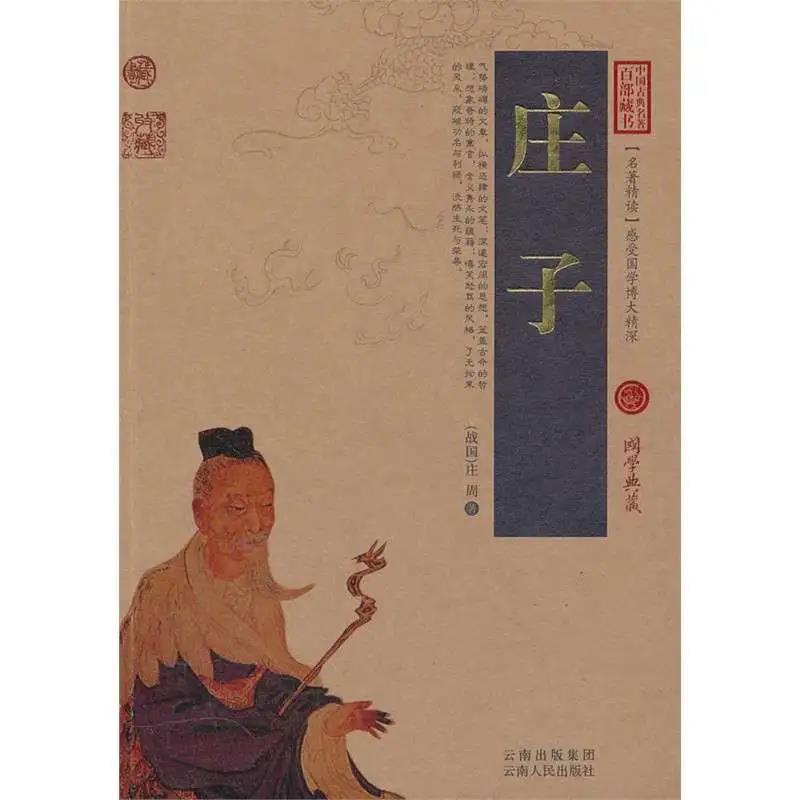
解生死之惑——
“齐生死”与“空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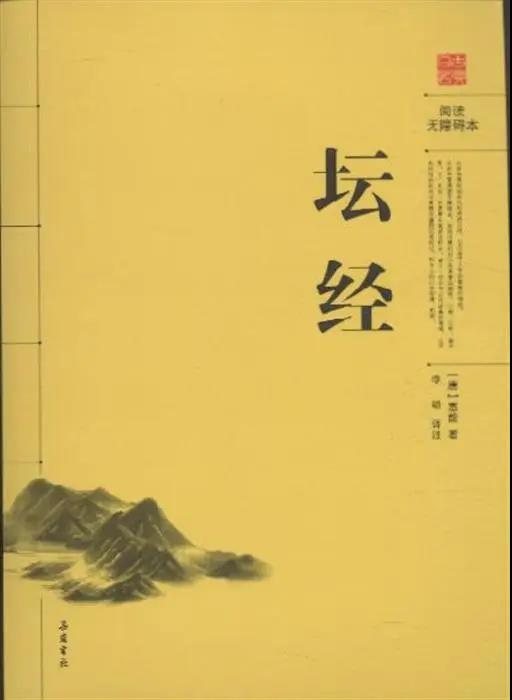
觅生存之道——
心之“游”与心之“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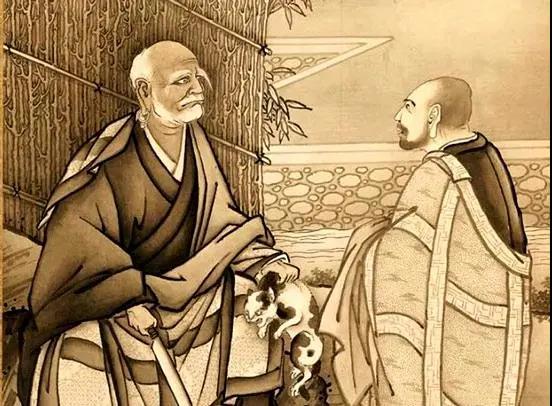
殝生生之美——
“无情、无物、无待”与
“无念、无相、无住”




结 语

注释

作者简介
陈守湖
陈守湖,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师从冯黎明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新闻传播研究。
内容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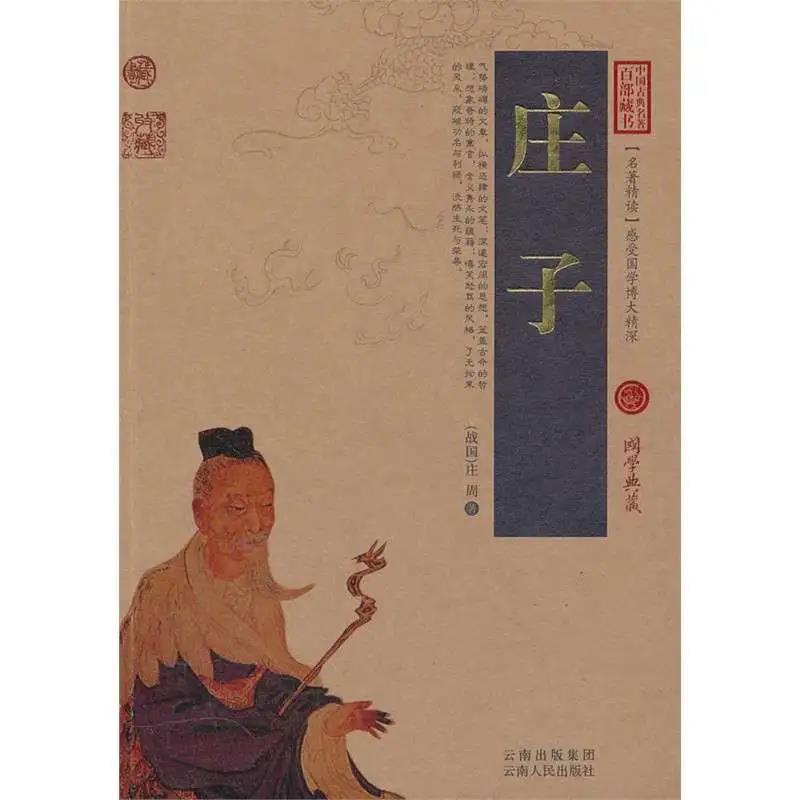
解生死之惑——
“齐生死”与“空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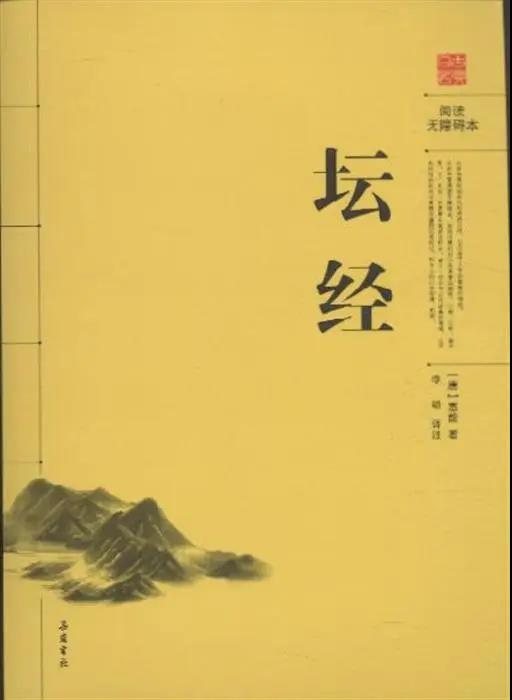
觅生存之道——
心之“游”与心之“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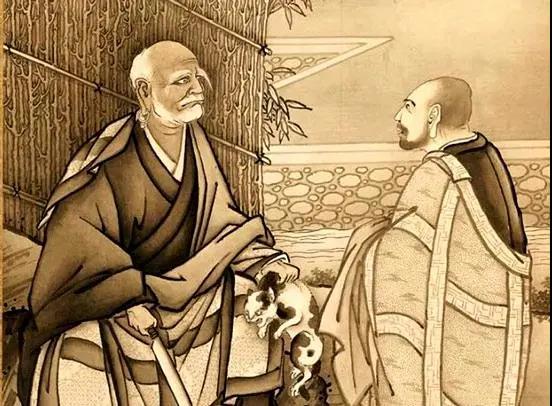
殝生生之美——
“无情、无物、无待”与
“无念、无相、无住”




结 语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