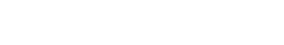编者按:
2017年上半学期,核心通识课程《简明世界史》实行以探究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为中心的小班研讨。在第三次关于世界重要历史人物的小班讨论中,各位来自不同院系的同学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与学科特点,选取各具魅力的历史人物,分成九个小班,小班内又分成若干小组,广搜博采,积极思考,并在课上将小组的探究结果向大家展示。编者从中选取了牛顿组代表、来自经济与管理学院2016级的李思瑶同学的课程展示与诸位读者分享。
牛顿研究神学从来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过程,所谓牛顿从晚年“开始”研究神学之说也缺乏进一步的考证。牛顿对于神学的思考与研究贯穿了一生,从幼年时期长辈的影响开始,到以后环境的熏染,《圣经》的“指引”,最终使其在神学之路上一去不复返。

一、踏上神学之路
1.幼年时期的影响
(1)长辈的影响:
牛顿的舅舅痴迷神学,他在与舅舅的接触过程中,受到舅舅说教的影响。随后母亲改嫁,其继父收集了很多基督教的书,也留给牛顿一本写有几个尚未完成的神学标题的空白笔记本,这个本子伴随了牛顿很长一段时间,其上面遗留的神学思想与问题可谓牛顿的神学“启蒙”。
(2)导师的影响:
巴罗是牛顿在剑桥的导师,牛顿曾经师从巴罗并且后来做过他的助手,也正是巴罗发现了牛顿的天才过人之处,提升了牛顿在光学和几何学上的造诣。可能囿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巴罗对于神学有额外的关注,这种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牛顿,使牛顿加深了对神学的关注。
2.《圣经》
(1)“圣经密码”的奥秘:
“圣经密码”,指的是在希伯来文《圣经·创世记》的开头,每隔50个单词就可以拼出“Torah”一词,泛指犹太教的全部律法教条。其中包括很多预言性的内容,比如世界末日、希特勒、纳粹、贝多芬等等,都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在文献中找到。这种方法在后世受到质疑,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偶然,实际上可以找到所有自己想要找到的词汇。但是经过多位顶尖数学家验证后,发现这种方式并不是撞运气的假说,因此尽管存在质疑,却也找不到反驳的依据。牛顿终生致力于这种思想和预言的研究,相信《圣经》里暗藏着人类历史的预言。但遗憾的是,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破译出神圣的预言。
(2)《圣经》与其他学问的结合:
牛顿拥有数十本不同语言的《圣经》,每本他都曾反复阅读,并总结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犹太《圣经》最为标准。他还认为《圣经》是“神之书”,透过这本书可以研究神学、研究历史、推断过往等等。同时,作为一名不无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基督教徒,他将教会史及古代人类史研究、《圣经》诠释学、千年至福说的考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整体看法。
3.思想
(1)异教徒:
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牛顿从小就是有宗教信仰的教徒,并不是只从晚年才开始信仰基督教。同时,他一生中80%的著作都是和宗教神学有关的。但是,牛顿作为一个牛人存在,他信教信得和别人不太一样。他不是纯粹而一般的基督徒。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①牛顿不相信耶稣是神(God)。他不相信“三位一体”理论(基督教神学信条,圣父、圣子、圣灵三者是一个独一、真实、永恒的神的三个位格)。他也不相信不死的灵魂。
②牛顿认为《圣经》是一部圣书,他将多种语言的《圣经》读了好多遍,也试图发现《圣经》所隐藏的信息以及尝试解释《圣经》的含义。他在《圣经》方面的造诣几乎无人可比,这其中就包括神学研究。
(2)试图通过神学解释上帝:
有人认为,牛顿一生的目标就是在解释上帝。为了解释上帝的存在,牛顿前半生主要投身于自然科学,却也没有忽略神学。而后半生则认为神学对于上帝的解释更加强有力,所以研究方向转向了神学。
二、一千零一个成果
1.三种“反对”思想:
反三位一体,反对道成肉身(耶稣降世拯救罪人),反对耶稣神性。牛顿认为,三位一体的独一性很难调和,三位一体思想之所以能确立是因为外来思想的影响和政治管理的需要,并非其本身的真实性;“道成肉身”则把上帝变来变去,亵渎了上帝的永恒;而崇拜耶稣是一种“神像崇拜”,是一种基本的罪。牛顿视上帝为一位强大的创造者,但是他不同意上帝会造出一个完美的世界而无需他的干预。
2.数学与神学的合体:
牛顿认为日心说和万有引力等数学方面的发现,和宗教、神学是相辅相成的。具体而言,这两个自然科学规律是原始基督教和早期哲学的起源。牛顿的目标是用数学来证明基督教的合理性以及源头。同时,在1713年修订的《自然科学原理》中,牛顿曾编了一个附录,加了一些神学思想在他的太阳系模型中,即科学和自然的美一定是在有超越自然的智慧和力量的控制下形成的。在再版的《光学》中,牛顿也添加了类似的神学思想,即在动物和太阳系美妙的一致性中肯定有超越自然的智慧的媒介的干预。
3.出版《Chronology》(年代学):
《Chronology》是牛顿总结编写的关于基督时间线的神学之书,这部书的厉害之处在于它颠覆了《圣经·旧约》的编年顺序,从而颠覆了基督教乃至人类文明的时间线。牛顿之前,众教关于基督时间线的说法众说纷纭,直到牛顿决定插手。他觉得只有犹太人的《圣经》是靠谱的,于是就试图将自己的理论和犹太《圣经》相结合,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文明开始于埃及人,即公元前1125年左右。
《Chronology》在出版一两年后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被誉为和牛顿的《Principia》、《Opticks》齐名的作品。牛顿的神学研究体现了与他在其他研究领域同样的创新思想和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Gibbon甚至宣称只要《Chronology》这一本书就可以让一个人名垂千古。
三、对神学研究的评价
牛顿在神学方面的研究之所以没有他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研究般令人瞩目,是因为神学研究并非大众所熟识的领域,而且它还涉及信徒的个人信仰和想法,与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且,神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力也远不及科学研究。另外,牛顿转向研究神学,在某种层面上似乎也辜负了世人对他的期望。牛顿44岁时便写出了影响人类文明的著作,但余下的几十年里他便投身于研究《圣经》,没有符合大众的预期。其实,现在依然有人在研究神学这种“奇幻”的哲学,拿神学博士学位也比拿物理学博士学位要困难得多。但是我们不应该把牛顿转向神学研究看成是他人生的堕落,而应当是他又一个大放异彩的宏伟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