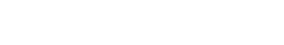2019年3月18日上午9:00,通识教育大讲堂第十二讲在武汉大学樱顶老图书馆拉开了帷幕。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以全新的视野重新定位了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并提出以现代性原则来反思、评估传统文明,对我们正确理解和对待中国文化具有启发性意义。
本次讲座由武汉大学哲学院苏德超教授主持。讲座开始前,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建中教授向黄裕生教授颁发了通识大讲堂主讲人纪念证书。

讲座伊始,黄裕生教授从中国文化的现实处境出发,提出了重估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异文化的强烈冲突和挑战迫使中国人摆脱原有的“文化中心主义”,尝试着重新定位自己的文化。而西方世界为我们的重估提供了两个参照系统:一个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世界本原文化体系;另一个是构成现代性社会秩序基础的原则体系。二者缺一不可。

黄裕生教授认为,对于中国文化地位的认识,并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需要放到世界史的普遍性意义上去思考。他借鉴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认为更准确的定位应该是“四大本原文明”,而本原文明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对于绝对性的觉悟。他进一步解释道,一般文化所能够关注到的大多是一些相对性、有限性的东西,文化的突破恰恰就在于对于绝对性的觉悟,这种觉悟可以通过宗教和思想两种方式来实现。东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正是依赖于这种强烈的绝对性力量;第二是对于人自身普遍性的认识。劳动分工使得人自然地生活在等级秩序之中,受到等级关系的制约。本原文化的超越性就在于发现了人具有更普遍的本相,而不只是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因此,本原文化自觉地承担起在人与人之间贯彻普遍原则的使命;第三是对于人自我改善实践的自觉。在前两种觉悟的基础上,人需要对自身进行自我提高、自我改善的实践,即独立求知、独立为学,与此同时相信教育具有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暴力。

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本原文化,体现出以上三个特征。首先,在绝对性方面,殷商的崇拜体系确立了“上帝”作为超越自然神的最高神,同时切断了人神交易,以宗教方式获得了关于绝对性的觉悟,并使得宗教生活纯洁化。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则以思想方式加强了这种意识,例如墨子的“法天”之说。其次,在人的普遍性方面,最典型的就体现在儒家思想之中,尤其是孔子的“人学”原则。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他率先提出“仁者爱人”,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终身法则,既承认每一个他人都是独立于自己的又一个自己,又尊重并维护他人作为这样的个体。最后,在自我改善方面,孔子所确立的学说帮助人成为君子,抵抗住各种诱惑,而成为君子必须通过教育与知识。以上三个标准确认了中国文化是一种本原文化,而这也是中国文明源源不断的根源所在。

黄裕生教授进一步指出,本原文化民族往往是苦难深重的民族,因为它自觉地要去承担世界的普遍性原则,这是一种内在的使命。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就源于此,他们面对异文化的挑战,陷入了无法完成文化使命的迷惘。到了今天,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我们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其他国家文化。他认为,本原文化之所以为本原文化就在于对绝对性的觉悟,但是绝对性是永远无法被揭示出来的,所有本原文化都只是对绝对性某一方面的一种解释、一种叙述、一种确立,这就意味着本原文化之间都必须相互学习,才能真正丰富自己,才能体验到绝对性的更多特点。近代以来,不同文化的思想碰撞不仅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建立起一套关于人自身的原则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最根本的身份——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格主宰,由此延伸出人的责任、权利优先、主权在民等原则理论。而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在这样一套原则体系之下,重新反思、评估、理解我们的本原文明,正确判断和评价传统文化,这就是古今之变的内涵。

在提问环节,黄裕生教授耐心地回答了观众的问题。其中,有同学提出古今文化是否具有高低之辨,黄裕生教授认为文化之间确实具有高低之分。文化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对人的自觉性的认识也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常常用东西之分来模糊掉古今之变,实际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文化不仅具有类型的差异,也存在着代际的变更,历史处于一个扩展的历程之中,我们必须重视这一点,才能不断提高。
黄裕生教授的讲座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启发我们进一步理解和反思自己的文明。实际上,我们在思考问题时需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在全球化和世界性的高度上来评估,才能提高和完善自己的认识。讲座虽然结束了,但关于人和文化的思考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