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作者
石云里
石云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研究所客座研究员,Annals of Science(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编委,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历史仪器工作组主席,中国科学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包括天文学史,物理学史,科学思想史,中外科技交流史。
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西方通识教育的启示

►图片来源:Unsplash
近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上空,一直漂浮着两朵乌云。第一朵是钱学森在2005年,对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第二朵则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在2008年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回答采访者时,道出的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 ‘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
“钱学森之问”对国家的发展固然至关重要,但毕竟只涉及到人才培养金字塔的塔尖。而“钱理群之忧”则涉及到这座金字塔的整个塔身——接受过教育的所有公民。
钱理群所忧虑的结果,其实已不断出现:陷于贪腐的大小官员,专靠赚黑心钱发财的老板,在媒体上发表不负责言论的无良写手,还有动不动就在国内外公共场合制造出各种悲喜剧的“中国巨婴”……
所有这些人都或长或短地接受过学校教育,很多人甚至还是大学和研究生毕业。
“钱理群之忧”所涉及的,其实就是一个“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是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
从通识教育起源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培养什么样的人”一直是其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以至可以说,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通识教育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
通识教育,也许是解决“钱理群之忧”的方向。
“美国从何而来?”与通识教育的兴起
通识教育是1917年到1919年之间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关口,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要介入世界大战很是想不通,表现出了抵触情绪。美国政府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从教育上着手解决,于是决定出钱资助大学,让他们开一门叫“战争问题”的课。
这门课主要宣讲美国的政策,解释美国为什么要介入这场战争:美国继承了西方文明,而现在西方文明受到了威胁,这场战争不是哪个洲的地域性问题,而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问题。
一战结束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开设了相关课程,以继续引导学生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自何方,我们的文明继承自何处,我的文明反映了人类共有的何种东西?也就是培养学生对于欧洲文明及其价值的认知与认同。
这种做法受到政府的认同,并被其他大学学习。
之后,二战快结束时,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柯南特(James B. Conant, 1893—1978)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大学教育的讨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大学培养的人才在战后如何成为西方文明的维护者。

►詹姆斯·柯南特
他认为,科技进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大大加快,也使社会随之发生急速的变化,导致社会阶层高度分化,人们的意志无法统一,社会不能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他对此深感忧虑,想通过大学的通识教育来培养未来社会精英们的社会责任感。
于是,柯南特在哈佛推动了一场课程体系改革。他任命了一个由13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讨论“自由社会中通识教育的目标”问题,并在1945年形成了一份报告,题目是《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报告将学校教育分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指出:“通识教育指的是学生全部教育中使其首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部分,而专业教育则指使学生具有某种职业技能的部分。”
也就是说,通识教育所要解决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的问题,而专业教育解决的则是职业技能的问题。具体到美国学生,报告强调要通过通识课程向他们传达“三个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历史——美国人是从欧洲而来;共同的现在——大家走到一起形成美国社会;共同的未来——我们还要一起走向未来。
报告希望通过传达这些理念使学生明白,西方文明是当前人类最好的文明,所以要继承它,并成为它的捍卫者。而一个学生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了解人类的历史,具有历史的眼光与意识;需要了解财富的形成,掌握相关的基本经济原理;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科学精神,等等。
报告以及哈佛大学的这场改革影响巨大,标志着所谓“通识教育运动”在美国的兴起,而这份报告则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是“通识教育运动的’圣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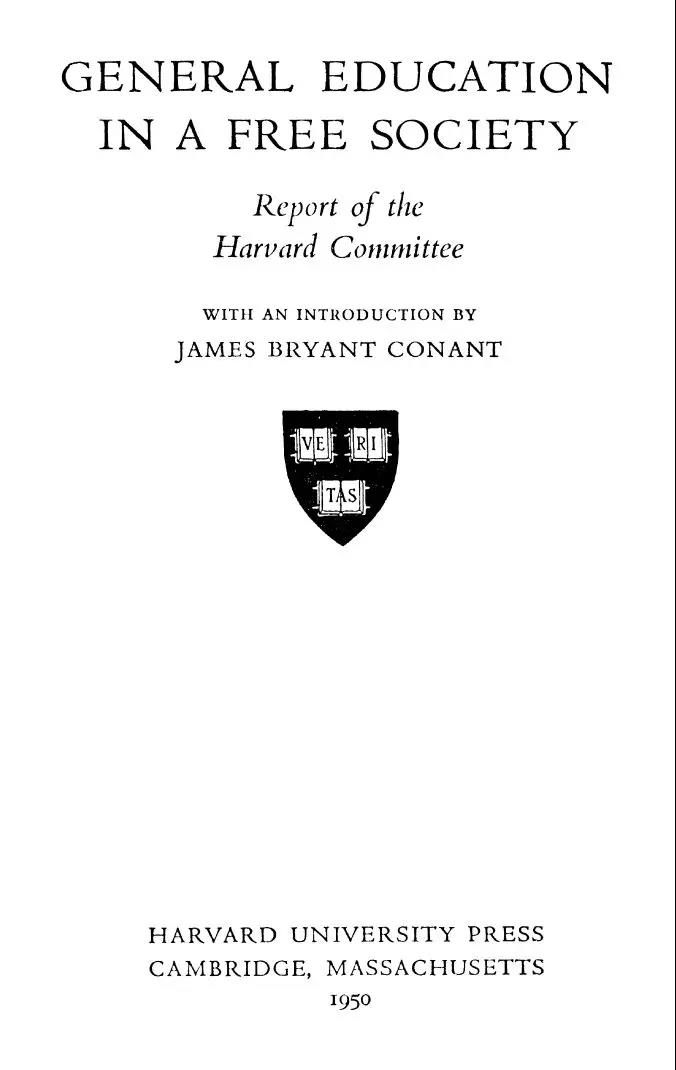
►《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
1947年,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的《为了美国民主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Democracy)报告也强调了通识教育重在全面育人的观点,指出:“通识教育是要给学生某些价值、态度、知识和技能,使其在自由社会中生活的正确而美好,要让学生对其现实生活中的富丽文化遗产、现存社会中的可贵经验与智慧能够认同、择取、内化,使之成为个人的一部分”,使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称职的父/母亲,一个健全的公民”。

►《为了美国民主的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上述两份报告奠定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理论基础,使之得到更加广泛的推行。
此后,美国各主要大学都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对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作出调整和改革,但“培养什么人”始终是关注的中心。
自由人教育和人文教育
在柯南特等人看来,通识教育并不是全新的东西。他在《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导言中指出:“通识教育问题的要害就是自由与仁爱传统(the liberal and humane tradition)的继续”。确实,这种以解决“培养什么人”为中心的通识教育与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教育在旨趣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而后者又是对欧洲古代与中世纪文科教育进行改革的结果。
欧洲古代与中世纪教育中的文科包含在“自由人课艺”(Liberal Arts)之中,包括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乐律,是自由民所要接受的基本教育。它们在当时都被视为一位自由人市民生活(civic life)所必备的知识,但其中并不包含任何关于人格与人性塑造的内容,因此都是工具性的,一个“艺”(Arts)字已经将这一层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为了医治当时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也为了满足新兴公民阶层的文化需要,出现了一场针对文科教育的改革运动。正如当代教育史家C.W.凯林道夫所指出的:这些改革者们“反对(中世纪流行的)这种对教育的实利主义态度,他们相信,教育应当有道德的目的,应当使年轻人适合于在宫廷和公众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相信,达到这一结果的最好方法就是男女青年潜心于古代的优秀著作,尤其是诗歌、历史、雄辩术和道德哲学。……旨在造就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有德性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已经读过古代美德的有权威性的榜样,并以此自期。他们是深思熟虑的,因为他们通过学习历史将人类的经验延伸到了遥远的过去。他们将是能言善辩并能将美德和深思熟虑传达给别人的人,因为他们研究了过去最雄辩的作家和演说家”。
所以,这批改革者世纪建立了一种新的文科教育体系,内容包括诗歌、历史、道德哲学和雄辩术,而其中雄辩术实际上包含了传统的语法、修辞与逻辑等传统文科内容,在教授方法上主张以阅读古典为主。
这批教育改革者仍然沿用古代“自由人课艺”的说法,但却把“自由人”理解成“不需要为图谋生计而工作的人”。
为了突出这种新文科体系对“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的强调,这些人借用了罗马拉丁文中的“人文”(humanitas)一词,把由此形成的新式文科称为“人文学”,也就是拉丁文的studia humanitatis。“人文”一词对应于希腊文中的“仁爱”(philanthrôpía,对使人成其为人的特性的珍爱)和“教养”(paideia)两重意思。
到了十九世纪,这批改革者的理念被称为“人文主义”(humanism),而他们本身也就成了所谓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利用这些新名词,我们可以说:这批教育改革者所创立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新文科教育,从而使文科变成了“人文学科”(humanities)。
与传统的文科相比,这种“人文主义”文科对文科作用的理解不再停留于功利或者工具主义的层面,而强调了它对人和人性的培养和塑造,强调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人具有美德并具备深思熟虑的生活态度。
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这种“自由与仁爱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从意大利传遍了整个欧洲,对欧洲近代教育的发展和近代社会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与弥合
上述的人文主义文科教育并不排斥理科。相反,它十分重视理科知识在人的培养中的作用。这就不奇怪,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潮对欧洲近代科学的建立也起到过十分关键的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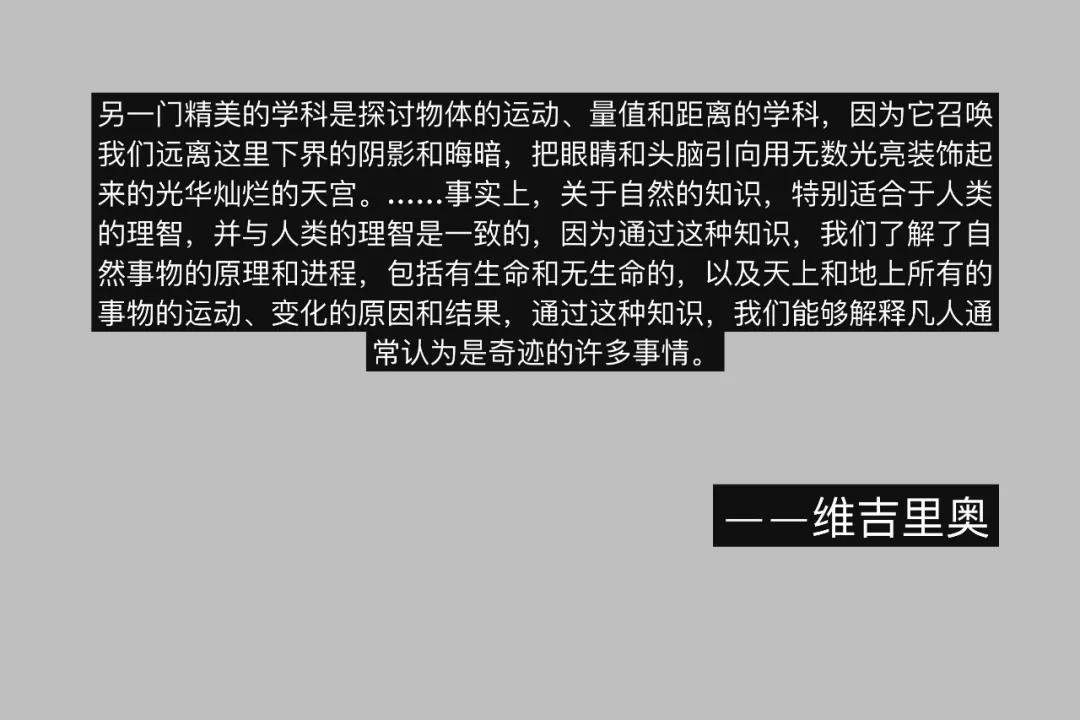
欧洲近代科学的出现与迅猛发展导致了以近代科学方法为基础的技术革新热潮,并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随着这一切的发生,人文学科与科学学科之间却出现了断裂,并且鸿沟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并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
用现代科学史之父萨顿(Geroge Sarton,1884-1956)的话来说,“由于旧人文主义者的冷淡与疏远,也由于某些科学家的狭隘,不过首先还是由于掠夺成性者不知足的贪婪,产生了所谓‘机械时代’的罪恶’”。后来,才有学者明确地把这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分裂,也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
作为一位乐观主义者,萨顿认为“这种‘机械时代’必然要消逝,最终要代之以‘科学的时代’”。为此,萨顿给这种“机械时代”开出了一个药方,他称之为“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萨顿试图用这种“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架起一座沟通人文和科学的桥梁,并把科学史作为这种“至高无上的人文主义的开始”。
在萨顿看来,新人文主义就是要经由科学史达成的一种哲学,目的是要实现历史知识与最新科学发现的结合,既将科学精神融入人文,又从人性角度看待科学,以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乔治·萨顿
他指出,“新人文主义是一种双重的复兴:对于文学家是科学的复兴,对于科学家则是文学的复兴”。萨顿所说的“文学”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科或者传统人文学科。
萨顿认为,弥合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达成这种新人文主义目标的途径是对人的教育,这种教育甚至不光局限于学校教育,甚至还包括“一个人由生到死的整个教育”。他还指出:“可以说组织科学史的学习和教学形成了这种(新人文主义)运动的核心。”
萨顿甚至为这种教育的内容制定了计划,指出科学史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科学史教育人才的培养提上日程。
一战结束后,科学史在哥伦比亚和芝加哥等美国大学开始受到重视,这就给在1915年移民美国的萨顿实现其理想提供了某种土壤。1945年哈佛大学推行通识教育改革时,萨顿的思想与柯南特的改革目标可谓一拍即合。柯南特也把科学史当做医治科学教育中“深奥而高度专门化的学者知识”的一剂良药。
哈佛大学将萨顿从讲师晋升为教授,而且对非科学专业学生的科学必修课改成了5门新课,其中有四门主要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讲授,包括萨顿开设的科学思想史课,主要讨论科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及重大科学思想的知识与社会氛围,及其哲学背景与内涵”,柯南特则亲自主讲“实验科学成长史”,其讲义《哈佛实验科学史个案研究》(Harvard Ca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Science)成为当时科学史领域的一部名著。
哈佛的做法很快扩展到美国的许多其他大学,而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1955年将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列入资助范围,标志着科学史在美国的成熟与职业化。
当前中国教育亟需新人文教育
“钱学森之问”与“钱理群之忧”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现行学校教育中所真实存在的关键问题,一个涉及顶尖人才的培养,另一个则涉及更加广泛的公民精英的培养,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习近平讲话)。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起源于欧美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所要解决的最根本性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而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人文教育理念也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量身定做的,是一种关于人性塑造的人文主义的文科教育。现代欧美通识教育的体系虽然已经发展得更加庞大,但这种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减弱。
按照今天的定义,文科在中国起源很早,不仅周代用于培养贵族的“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中有(至少“五礼”和“六书”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的“六艺”或者“六经”也是纯粹的文科。但是,这些文科可能都应划入功利主义文科的范围,而算不上是人文主义的文科。
首先,它们与欧洲古代的自由人教一样,目的是为了培养贵族或者少部分社会精英,而不是广大的社会公民;其次,当儒学变成科举考试中的唯一科目时,被儒学主宰的文科教育也就基本上变成了功利主义文科,也许只有少数私人书院才算例外。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文科教育一下子被西学冲击得七零八落,文革更是给了它最后的封喉一剑。与此同时,西方人文主义的文科及其精义则因水土问题落地艰难,并且在冲突与调和中也受到各种方式的肢解。即便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应试教育系统的疯长与弥漫,中国的文科教育更变成了功利主义与工具主义的附庸,真正以人的培养为本的人文主义文科教育始终踪影杳渺。
当然,我们不敢说人文主义的文科教育会让受教育者百分之百地变成将具有美德并具备审慎生活态度的现代公民,因为整个社会的大氛围和基本制度的影响力可能更大。但是,这种教育肯定能帮助我们大大减少人性方面“劣质产品”的数量,社会人口的一般修养也会因此得到很大提高,中国也才能够真正进入现代社会。
中国当下教育中所需要的首先应该是真正以人的塑造为中心、但在中国教育系统中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或者实施好的人文主义的文科。另外,作为对现代公民的人文主义文科教育,我们还需要加入科学精神这一十分重要的维度。
欧美当今通识教育中除传统文科以外的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学、科技美学等等,还有数学、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等课程,无非就是想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把学生培养成同时具有道德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公民。
其实,萨顿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所要达到的也就是这样的目标,这样的教育应该就是当代的新人文主义教育的应有之义,其中所需要的文科教育就是我们所说的“新人文教育”,其主要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同时具备道德理性与科学理性,具备对真、善、美的认识和践行能力,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公民。
当然,新人文学科也应该包括利用科学方法来探讨人文问题的那些学科,如科技考古、数字人文、定量历史等等,这些研究其实也可以具体的实践和实例,向学生示范科学与人文结合的可能性与重要性。
本文是根据2018年10月13日作者在南方科技大学“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建设高峰论坛”上的主题报告整理而成。
参考文献
[1] 关增建.《他山之石: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解读》. 上海交通大学,2018.
[2] The Committee on the Objectives of a General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mes Bryant Cona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50.
[3] Earl J. McGrath. The General Education Movement (An Editorial). 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Vol. 1, No. 1 (October 1946), pp.3-8.
[4] Christopher Hamlin. The Pedagogical Root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Revisiting the Vision of James Bryant Conant. Isis, Vol. 107,No.2 (2016), pp.282-308.
[5] [美] C.W.凯林道夫编. 《人文主义教育经典文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 [英]C.P.斯诺著,纪树立译. 《两种文化》. 北京:三联书店,1995.
[7] [美]乔治·萨顿著,陈恒六、刘兵、仲维光译.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8] George Sarton. The New Humanism. Isis, Vol.6, No. 1: 9–42.
以上内容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